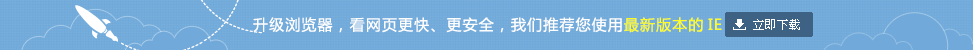從2008年上半年的搶奶風波,到三聚氰胺事件后的傾倒鮮奶,再到如今的四處送奶……一系列的事件讓這些奶農和奶企之間的關系在微妙地變化著。而在奶企臉色不斷變化的背后,奶農們也不斷變換著他們悲喜各異的面孔。
一個農村的養牛樣本
2009年12月31日,偏安高青縣一隅的付家村養牛基地內,隨處可以見到奶牛的身影。
孫軍亮(化名)就是付家村為數不少的奶農中的一員。與其他奶農一樣,孫的家也緊挨著他近年來所苦心經營的養牛場。
對于這個聚集了全村近四分之一村民的養牛基地,孫軍亮有著深厚的感情。按照他的說法,這個位于該村西頭的奶牛養殖基地是其擔任村支部書記時一手建立起來的。
對于當時涉足奶牛養殖并“舉全村之力”建立養殖基地的初衷,除了因看好奶牛養殖的“錢景”之外,政治感敏銳的孫軍亮稱,當時田鎮鎮政府出臺的“奶農向銀行的貸款,由政府出面擔保”的優惠措施讓他在資金方面“放足了心”。
事實上,作為牲畜養殖傳統大縣的高青出于增加當地農民收入的目的,對奶牛養殖的支持由來已久。早在1992年,高青縣政府就出臺了《關于大力開發秸稈資源,加快發展養牛業的決定》,鼓勵發展養牛業。而此后,在牛奶產量面臨巨大缺口的2001年和2002年,高青縣官方又相繼出臺了各種鼓勵措施。
當時,付家村也通過了“免收養殖小區內養牛戶三年土地租金”的決議。種種利好的刺激下,孫軍亮率先通過貸款購買了幾頭奶牛,“耗盡家財”一頭鉆進了這個被當時輿論認為是“小投入,大產出”的行業圍城里。
“執子之手,方知子丑”,這句現在流行的網絡調侃語或許能恰當地詮釋出進入奶牛養殖領域后孫軍亮的感受。在進入這個“外面看起來很美”的完全市場化的農業領域后,有著9年“領導生涯”的孫軍亮才知曉,并不是辛勤勞動就能致富,決定自己及其他養殖戶收入和命運的是變幻莫測的牛奶價格。
面對毫無規律可循的奶價,在這個“規模算得上大”的基地里,幾年前就有養殖戶因承受不住養奶牛的成本壓力,選擇了退出。“可惜啊,正好沒趕上那兩三個月的好時候。”孫深吸了一口煙感嘆道。
喜
搶奶潮下的高奶價
孫口中的“兩三個月的好時候”是在2008年上半年。
本報調查得知,在2008年上半年,因為原奶一時供不應求,作為奶牛養殖大縣的高青,一時也成為省內外諸多乳企爭奪奶源的主戰場之一。此時,高青全縣已建成標準化養殖小區126處,奶牛的存欄量膨脹到了2.83萬頭。“當時來高青搶奶的有蒙牛、伊利、三元、光明等大企業,也有省內的佳寶,當然也有本地的乳企。”孫提起當年的“搶手”情景頓時兩眼放光。
和其他奶農不同,孫軍亮還有著其他兩個身份。在養殖奶牛的同時,孫還與另外兩名村民合資購買了一臺擠奶設備,建起了負責整個養殖基地擠奶業務的奶廳。與此同時,孫雇了一輛運奶車,每天負責將奶廳所收集的牛奶送往各乳企設立的原奶收購站。
而他的特殊身份,也讓其成為2008年上半年各路奶企爭相拉攏的對象。“當時經常有奶廠的工作人員和區域經理過來做工作,極力邀請我往他們的奶站送奶。”孫軍亮頗為自豪地告訴本報。
在經過一番價格比較后,孫軍亮選擇將原奶送往當時設在高青黑里寨鎮的光明乳業奶站。不過,往光明送奶并未延續很長的時間。在爭奪奶源的高峰期,當地有關領導也受本地一乳企委托向這位送奶人打過招呼,“本地的企業缺奶很嚴重,應該優先照顧本地企業。”
在2008年上半年,“嗷嗷待哺“的乳企對各地送來的原奶也相當歡迎,并且逐漸放松了對原奶的檢測標準。對此,也曾給多家乳企送過原奶的孫軍亮表示,“當時我送幾車奶他們就要幾車,只要送去的奶,基本都達標。”
與此同時,在這場奶源的爭奪戰中,原奶的收購價格也隨著各乳企的較勁越升越高。“奶戶手中的原奶最高賣到了3.2元/公斤。”孫接著說道,“那時可能是我養牛以來原奶價格最高的時候了。”和孫的情況相似,其他多數奶農也隨著奶企的爭搶奶源而喜上眉梢。
愁
“無處安放”的牛奶
不過,孫軍亮等奶農臉上的喜色很快被“愁”字代替。
2008年9月份,三聚氰胺事件的發生,頓時讓國內乳企集體陷入低谷。而此時,孫和其他奶農也猛然發現,幾個月前被瘋搶的原奶價格更是一路下跌,此前兩三個月的好行情已不復存在。
“奶站的原奶收購價格一下子就從3.2元/公斤降到0.8元/公斤。”孫軍亮稱,這個價格與一頭奶牛一天吃掉10公斤精飼料的成本相比,奶農都是在虧本售奶。
與此同時,不久前還被各奶站奉為座上賓的孫軍亮悲哀地發現,此時的他已成為各奶站最不受歡迎的對象。
2008年上半年,本地一乳企曾與他簽訂了長時間的供應合同。然而,在三聚氰胺事件后,該乳企向他告知,“合同規定好的量將按照市場價格即0.8元/公斤進行收購,超出的部分的收購價為0.2元/公斤。”更讓孫摸不到頭腦的是,該乳企此時一改往日對原奶“來者不拒”的態度,新采取的檢測標準苛刻得“難以想象”。
面對乳企這種“變相拒絕”的措施,身兼奶農以及送奶者雙重職責的孫只能像無頭的蒼蠅般地指揮著送奶車到各個奶站處碰運氣。“但跑斷了腿也沒人要。”孫回憶起當時的情景仍唏噓不已。
而銷售不利帶來的巨大虧損使奶農的生意每況愈下。對此,這個見慣了牛奶市場波動起伏的群體采取了激進的“應對之策”——“倒奶”和“賣牛”。
“前年下半年,我們送去的2大車奶都因為檢測‘不合格’而被奶站拒收。沒辦法,我們只能把這18噸的原奶全部倒進村子后面的那條溝里。”長嘆一口氣后,孫很是難受,“當時心疼得不行,但是除此之外實在是沒有別的選擇。”
隨著“倒奶事件”的愈演愈烈,部分看不到希望的奶農也開始低價甩賣那些悉心照料多年的奶牛。然而,這些一度被他們寄予著致富愿景的“伙伴”在報出三折甚至更低價格后都無人問津。“15000元買的奶牛5000塊錢都沒人要,沒辦法,只能賣給屠宰場了。”
2008年9月爆出的“三聚氰胺事件”帶來的“熊市”一直持續到2009年的上半年。在此期間,孫一手建立起的養殖中心里,陸續有奶農退出改行的消息傳出。“老李、劉波等一共8戶不干了。”孫軍亮的媳婦數了數空置的養殖場后告訴本報。
暖
日漸回暖的奶業
就在奶戶養殖興趣漸淡紛紛賣牛之時,這位全村第一個養牛的農戶卻悄然從鄰居手中買下了5只小牛。對此舉,孫解釋說,“主要是看在朋友關系上幫他個忙,說實話,當時真不是看好后面的行情。”
不過,奶價卻出乎孫的意料,開始了觸底反彈。據18個省市地區的奶價價格監測顯示,2009年5、6月份,全國原奶平均價格已經回升至2.78元/公斤,到7、8月份,原奶價格升到2.87元/公斤,而9月下旬,原奶價格達到2.98元/公斤。“奶價確實是一點點地爬上去了。”孫軍亮表示。更讓孫軍亮振奮的是,在奶價重新高企下,似曾相識的奶源爭奪大戰再次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
據國內媒體報道,目前,各乳企在河北、內蒙古等產奶重地為爭奪奶源正激戰正酣。闊別一年多的無合同收奶、半路攔截、以許愿形式高價收購等“殺手锏”們紛紛重出江湖。對此,業內人士也認為,三聚氰胺帶給乳業的陰霾逐漸消散,國內乳業的復蘇和乳企巨頭間的新一輪“跑馬圈地”給予了奶價沖高的動力。
不過,據本報了解,這種情形尚未在淄博地區明顯顯現出來。“我現在去送奶仍然跟游擊隊似的,打一槍換一個地方。”這時孫的手機響起,他接完電話后無奈地告訴本報,“在本地乳企不要奶的情況下,我們的送奶車今天只能送往濰坊了。”
縱然銷路仍不比去年春天通暢;飼料價格也正在節節攀升——已有去年1900元/噸漲到了目前的2475元/噸,但正在慢慢回升的奶價讓孫等奶農看到了堅持下去的希望。
“照這個勢頭發展下去,我預測2010年下半年就能迎來乳業的春天。”這個資深奶農說道。
而去年市場上各乳企的大動作不斷似乎在回應著他的判斷:去年7月,伊利宣布在天津市濱海新區投資2.89億元,建設華北地區年生產4.5萬噸奶粉項目;此后12月,伊利再次宣布將在天津投資3.82億元興建酸奶、奶酪生產基地;而伊利在華北市場上的主要競爭對手三元集團也先后宣布將斥資5500萬元和6.8億元分別在河北以及北京大興區新建乳品生產線。
現在,孫軍亮圈里的30頭牛每天能給他帶來僅僅的30多元的純利。但比起過去近一年的虧本經營,這點“蠅頭小利”已足以帶給他些許寬慰。
已經堅守了7年的孫軍亮,一邊埋怨“從事著掙錢最少的養牛和風險最大的奶廳”,一邊又頗有底氣地重復著自己當前最主要的任務就是“養好牛、等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