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放量拐點未必是污惡化終點
王金南(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副院長)
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常態,高速增長向質量效益型中高速增長轉變,工業化進入中后期,產業結構不斷優化,主要重化工產品峰值初現,城鎮化增速放緩,這些都是有利于環境保護的因素。中國主要傳統污染物,如SO2和COD,疊加排放總量有望在2016~2020年之間(即“十三五”時期)達到峰值或下降平臺。借助后發國家在產業發展和環境治理方面的技術追趕和經驗借鑒方面的優勢,與發達國家在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左右出現污染排放拐點相比,中國主要傳統污染物排放出現拐點的時間,要比發達國家提前一些。
由于環境污染具有一定的累積效應,盡管主要傳統污染物排放拐點有望提前到來,但是,目前沒有納入總量控制的污染物排放量依然在上升。因此,我認為,排放量拐點不一定是污染“惡化”的終點,也不一定是環境質量全面“向好”的起點,而很可能是環境質量狀態為復雜的時期。如我國一些地區PM2.5下降,但是臭氧開始上升。這意味著,在各種污染物疊加排放處在高點的平臺期,中國反而需要以更低的收入水平,來應對嚴峻的環境質量惡化形勢。這是我們的挑戰。
我們與發達國家對比研究判斷,我國環境質量要想全面改善,如空氣質量達到國家二級標準,從全國來看,至少仍需要15年乃至更長時間。在“消化”經濟增長和城鎮化產生的污染增量的同時,需要大規模削減污染存量。因此,必須根據2020年小康社會目標,在平衡公眾環境質量訴求和目標可行可達的基礎上,確定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階段性環境質量改善目標。
我們要承認這樣一個事實:中國僅用了40年的時間,就基本上完成了發達國家100多年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進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增長成就。另一方面,我國卻用了大約30年的時間,“集聚”和“爆發”了發達國家100多年的復合性環境問題。如果我們也按照發達國家解決環境問題的時間去解決,能算什么本事呢?為什么不能用追趕GDP的速度,去加快環境治理的速度呢?
因此,我認為,必須要使拐點及早到來。拐點是指污染嚴重、環境質量差的點,而不是說環境質量全面改善達到國家標準的點。
例如,SO2在2006年出現拐點,那時的人均GDP只有2064美元。美國SO2達到峰值開始下拐是在1974年,那時美國人均GDP為1.1萬美元。當然,這也需要考慮匯率、通貨膨脹等因素。根據美國相關組織觀測的數據,2006年開始,中國上空SO2垂直濃度分布開始下降。這說明中國SO2減排是有成效的。現在空氣質量標準中,SO2標準有所提高,但是大部分城市的SO2濃度都不超標。當然,目前SO2排放的控制,主要是從PM2.5前體物的角度出發。所以說,中國的SO2排放量出現拐點,是真實并且可信的。需要說明的是,我的判斷依據是官方數據,可能不一定完全準確,而且從30年的歷史數據來看,有些地方與邏輯相矛盾。目前,經濟下行、基礎產業產量峰值和煤炭峰值出現,也都是判斷拐點的依據。
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并不。環保部政研中心王華表示,曲線與問題類型、區域、發展方式等都有關。另外,污染物排放、環境質量、環境影響(如健康)三者的EKC要區分開來。環境質量相對污染排放有滯后性,環境健康影響相對環境質量也有滯后性。當你在呼吸了10年有害健康的空氣,健康問題不一定很快顯現,可能是10年以后甚20年以后才出現。因此,我們不能看著庫茲涅茨曲線等拐點,更不能躺在庫茲涅茨曲線上“睡大覺”。
拐點有三種,間隔時間可能十多年
周宏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是一個統計規律,各國發展過程都基本符合這項規律。EKC曲線如同人的成長過程:人的個子先是快速長高,后又逐步變矮,中間達到一個峰值。為什么變矮過程與長高一側的增長速度不對稱?因為個子大且消化能力下降。發達國家的排放下降,是產業轉移的結果,而不是成本內化的結果。
EKC的縱軸有三種:強度、人均和總量,這三個峰值依次出現,中間的間隔時間可能相差幾年到十多年。
影響環境EKC曲線的因素主要有三方面:發展階段、能源資源條件(資源稟賦)和制度安排。發展階段和能源資源條件是自然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制度安排可以改變峰值的大小和時間的長短,但不能改變這種客觀存在。
對于數字拐點和事實拐點,屬于多少問題,而不是有無問題。對我國環境EKC曲線及峰值的研究意義,在于決策和效果評價,也影響形勢判斷。數據的可靠性是一個重要方面,想起鄭易生先生十多年前說過:虛假的數據經過模型精確計算,會得出什么結論,誰能說得清楚嗎?
不能把拐點沒到當做不作為的托辭
陸冬森(國家發改委環境資源司環保處處長)
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從本質上看,是個多變量函數,并不是分析與單一變量的關系,只有當變量成為函數的主導變量時才有意義,就像核磁共振切片。環境管理力度、能源和產業結構、技術進步、經濟總量等都是體量相當的變量,哪個因素都不能成為主導變量,不能過度分析解讀。現在該做的應像化療一樣,在身體(經濟社會全局)吃得消的前提下用藥,即落實環保法律法規,加大環境管制力度,而這也是污染物排放量的主導變量。
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是一種統計現象,而非環境經濟關系的必然規律,更多體現了環境管制的意愿和能力,我們不能在曲線上等拐點。發展有害論、發展對環境的庫茲論是兩個觀點,不能作為環境管理上不作為的托辭。
應多關注曲線的積分意義,它基本可以表征一定技術經濟和環境管制意愿以及能力條件下,城鎮化、工業化過程中應承受的環境代價。我國的城鎮化和工業化發展,壓縮在一個較短時間內,決定了其峰值必然高。所以,應進一步加強環境執法和管制,同時適當控制城鎮化工業化的節奏。
數字拐點來了,事實拐點還沒來
駱建華(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秘書長)
拐點實質分為兩種:一種是數字拐點,根據官方公布的數據;一種是事實拐點,考慮的是環境質量。按官方統計數據,2006年SO2排放量已經出現下降。這就是數字拐點,似乎證據充足,并以全國酸雨面積減少加以佐證。但我并不認同,理由有三點。
,煤炭消費總量由2005年的23億噸,上升至2014年的40億噸。其中,2005年電力耗煤11億噸,非電耗煤12億噸。2014年電力耗煤18億噸,非電耗煤22億噸。也就是說,2014年非電行業耗煤,已接近于2005年全年耗煤總量。從目前實際情況來看,非電行業除部分鋼廠上了脫硫設施外,其他行業脫硫甚少。因此,2014年非電行業SO2產生量接近于2005年全部SO2產生量。不妨做一個假設,考慮到2005年剛剛推行電廠脫硫,2014年非電行業也脫硫甚少,可認為兩者排放量相當。如果假設成立的話,2014年電力行業消耗的18億噸煤所排放的SO2總量,即是近十年來SO2排放新增量。
第二,環保部門近十年開展污染物減排,采取的策略是,模糊總量,核實減量。也就是說,忽略污染物總量,而現在公布的數據恰恰是,在2005年各省市上報的基數上,每年通過凈減量——新減量減去新增量,只是在原有基數上逐年遞減的結果。
第三,電力行業脫硫措施嚴格能夠做到達標運行。但其余一些小火電可能并沒有達標排放。據廣東一家脫硫公司透露,他們給電廠安排的脫硫裝置,真正達標的只有30%,實際運行的只有20%。此外,據了解,一些搞在線監測的公司,也幫助電廠數據造假,蒙混達標過關。類似情況很難統計。
根據以上三點,我認為,中國污染物排放的事實拐點并沒有出現。這與空氣質量每況愈下、霧霾天氣頻繁發生的事實相吻合。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是統計規律,中國也應該符合這一規律,只是拐點現在還沒到來,更不是2006年(官方開始節能減排起始年)就已出現。如果說,所謂一些學者判斷,鋼鐵、水泥等兩高一低產品峰值點即將出現,這也僅預示排放拐點即將到來,而非已經到來。
中國何時出現污染排放的事實拐點,我判斷,取決于三個因素:一是未來經濟增長速度,也就是政府采用何種手段保持經濟增速;二是重化工業產業何時停止擴張,鋼鐵、水泥何時到達峰值點;三是中國能源結構何時做調整,煤炭消費占比真正下降。
環境質量拐點會滯后于排放量拐點
王志軒(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秘書長、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委員)
,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是經濟社會不斷由低級向發展的過程中,環境污染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規律性,雖然發展總體上是螺旋式上升,但是在一定階段會有反復,所以EKC曲線也有不同的形態。尤其是把曲線的時間軸劃得較細時,曲線會有鋸齒出現。由于它所揭示的是“規律”,所以“先污染后治理”是規律,且是通過統計學印證的規律。
“先污染后治理”符合辯證法,符合人們認識事物的基本規律,無論人們是否愿意承認,絕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多數情況下,發展時首先想到的是發展目的,即便事先考慮環境影響,也受到人們認知水平的影響,不一定能夠認識清楚,也難有合適的治理對策,何況還要投入治理成本。
比如早期對河道裁彎取直工程,人們并不清楚其生態影響,多氯聯污染也一樣。但是,我們不能以此理論為借口,拖延與當時經濟水平相適應的環境治理。作為后發國家,我們可以吸取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反思我國的情況,并不是沒有機會做得更好,而是的確沒有做好。
我認為,我們可以在取得經濟發展成就的基礎上,同時做到環境質量比現在要好。特別是一些惡劣的環境污染行為,社會承擔的環境成本遠比社會收益與個人收益之和還要多幾倍;一些重大的環境政策決策,消耗過大的行政成本和社會資源,但沒有做到相應的環境質量改善。
第二,能否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應該分開解釋。從社會規律來看,我們無法避免,這其中一個原因是,新的環境問題不斷涌現,即使一些發達國家也不能算完全成功。如今年3月的巴黎霧霾。我們制定治理措施的目的,不是完全杜絕霧霾,因為那樣代價太大,但是,我們完全可以避免別人已經犯過的錯誤和走過的彎路。例如當前,不同污染源和多污染物的達標排放,這一經驗性管理措施,我們并沒有做好,卻急于把主要精力轉移到主要污染物總量控制,這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走彎路,甚至有簡單、粗放式環境管理之嫌。
中國環境問題的特點,與中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有不可分割的關系。如果我國還是計劃經濟,環境污染不會如此嚴重,當然,經濟社會發展也達不到今天的高度;如果是典型的市場經濟,也稱為法治經濟,環境污染也不會這么嚴重。在轉型過程中,我們更習慣使用計劃經濟的管理思路和方法。我國環境污染特征跟產業結構、地區結構有明顯關系,可以明確體現轉型過程特點,這也是經濟社會轉型付出的代價。
第三,中國目前處于曲線的什么位置?首先,EKC曲線只能是一個趨勢性判斷,由于曲線體現的是統計性規律,各國由于發展階段、地域及時代特點不一,具體情況完全不同。所以,各國典型曲線的可比性不大。
我不贊同根據人均GDP數值判斷拐點。中國是一個環境質量、資源分布、社會發展很不平衡的大國,一個省(市)的人口、經濟量可能相當于一個中、小型國家,國內各個省份之間的差距,比歐洲各國間的差距可能還大。換句話說,綜合判斷中國EKC的情況,就像把歐洲與非洲加起來判別一樣難。
從整體上判斷,我認為,我國污染物排放量可能到了一個顯著的拐點時刻,但今后可能還會有一個小的反復階段,這個拐點的時間點大概為三年左右,很難用一年來衡量。依據是:(1)黨的十八大后,國家明確了市場化和法治化方向,大力度進行改革推進,推行以壯士斷腕式的新環保管理體制;(2)霧霾引起全社會對環境的關注和對良好環境的渴望;(3)經濟進入新常態,我國連續30多年的經濟發展速度高達10%,有了良好的經濟基礎。同時,產業結構、經濟結構、社會結構的轉型迫在眉睫,否則將陷入“中等國家陷阱”。所以中高速的發展很快將過渡到中低速發展,與此相對應,能源消費總量及相關生產資料要素總量增加速度比經濟增速更低,其彈性系數會在0.5%左右甚至更低;(4)污染治理的道德環境、社會環境、法治環境將會明顯改善,過去“隱藏”或“隱瞞”的污染事實,反而成為未來污染降低的潛力。
我理解的拐點是實際污染排放量的拐點,與統計數字排放量拐點不同;而且不是環境質量改善拐點,尤其不是環境中細顆粒物改善(因為不僅是排放造成)、土壤污染、地下水污染的拐點。環境質量的拐點滯后于排放量的拐點。
第四,我國的環境問題與發達國家難有可比性。當今的技術水平與過去差異太大,幾十年前,互聯網、手機普及度很低,可再生能源發電也不像現在這樣普遍。而且,各國能源結構不同,發展道路也不相同。如我國PM2.5的組成、地區分布與發達國家也不相同,所以只能分項對比。這樣才能找出問題的原因,制定針對性措施。
例如,現在我國電力大氣污染物排放績效比發達國家還先進,中國煤電的凈效率是38.6%,美國是34%左右。但是,我國散燒煤的用煤方式,如冬天農村的土暖氣,可能與發達國家上世紀30年代差不多。但是,現在發達國家基本上沒有散燒煤,很難比較。
發達國家發展初期,污染狀況也很糟糕,日本由于大氣污染,甚至出現大白天汽車開燈的情況。但不少發達國家的階段性污染特征比較明顯,而我國的主要污染問題橫跨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如秸桿焚燒、農村居民用能問題。
我國是否能夠提前跨越EKC峰值很難說清楚,因為前提條件太多,而且,“提前”的時間基準是什么?我國本應做得更好,關鍵是要解決好污染控制的“兩級分化”問題。一方面,對某些企業要求污染物“超低”排放,或者用天然氣替代排放很低的燃煤熱電聯產電廠,不論從環境還是經濟,都得不償失;另一方面,對大量的散燒煤炭或者超標排放的車輛無有效監管。1980年,我國燃煤消費量大約6億噸,而現在我國原煤消費量約40億噸,僅散燒煤大約就有8億噸;發達國家煤炭轉換電力的比重在90%以上,而我國卻只有50%~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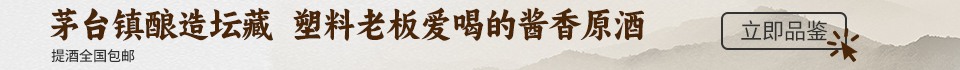





 簡繁切換
簡繁切換